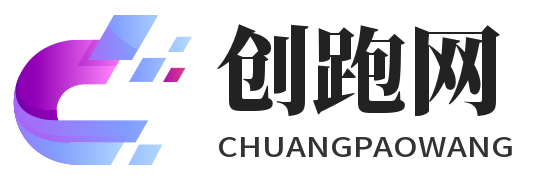老屋的院子里有一把磨得发亮的藤椅,那是爷爷的“宝座”,每天傍晚,他总会坐在那儿,摇着蒲扇,眯着眼看夕阳,藤椅的扶手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,是小时候的我用玩具车“撞”出来的杰作,爷爷从不生气,只是笑着摸摸我的头说:“小鬼头,这椅子以后留给你。”
那时的我总嫌藤椅太硬,不如沙发舒服,爷爷却念叨:“这椅子啊,透气,夏天坐着不闷汗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从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糖塞给我,糖纸皱巴巴的,带着老人特有的体温,甜得让我忘了抱怨。

十年后,我长成了少年,藤椅依旧在院子里,只是爷爷的背更弯了,他依旧坐在那儿,但目光不再追着夕阳,而是追着踩着滑板呼啸而过的我。“慢点!别摔着!”他的喊声被风声扯碎,我回头冲他挥手,却看见他扶着藤椅缓缓站起来,又缓缓坐下——他的腿脚已跟不上我的速度。
某个周末,我突发奇想,把滑板推到爷爷面前:“爷,试试?”他瞪大眼睛,连连摆手:“这玩意儿是你们年轻人玩的!”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,他终于颤巍巍地踩了上去,我扶着他在院子里“滑”了半米,他笑得像个孩子,藤椅在身后轻轻摇晃,仿佛也在偷笑。
后来,藤椅的扶手边多了块磨破的皮——那是爷爷学滑板时蹭的,他再也没能真正学会,但总爱指着滑板对我说:“你这玩意儿啊,不如我的藤椅稳当。”而我终于懂得,那把硬邦邦的椅子为什么是“宝贝”——它承载着阳光、糖果,和一个老人笨拙却滚烫的爱。
藤椅和滑板并排放在院子里,夕阳下,一个影子静静坐着,一个影子飞驰而过;一个在讲过去的故事,一个在画未来的模样。